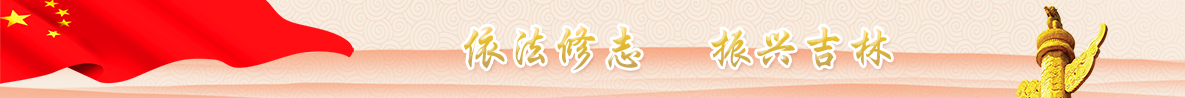
缸窑岭,一段民族手工业的沧桑史
发布时间:2017-08-21 15:14:00 来源:
字体显示:大 中 小
发端于清代中叶、兴盛于清末的吉林陶瓷手工业,到民国时期已呈遍地开花之势,具有一定规模的窑址有吉林缸窑、杉松岗同兴窑、中兴瓷业公司、兴隆山窑、凉水窑、瓦盆窑、平安窑等。
此时正值大规模移民潮之际,来自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闯关东流民将关内制瓷工艺带到东北,他们看准了民用陶瓷的广阔需求空间,兴办缸窑实业,主要生产缸、罐等民用粗瓷,也有碗、碟、酒具等部分青花瓷器,如今在吉林市的缸窑碳素厂、凉水陶瓷厂、平安镇陶瓷厂尚保存有完好的当年陶炉。
杉松岗是一道绵长的山岭,因早年岭上多杉松而得名。镇子位于辉南县东南部,距县城朝阳镇47公里,属丘陵半山区。坐落于此地的杉松岗煤矿素有“煤都”之称,但现已开采殆尽,留下大片沉降区,政府正组织分批向县城迁移。
就在杉松岗镇西部,缸窑岭的名字却渐被世人淡忘,这个存在了一百多年的缸窑尽管只剩下一圈垒石窑址和一位耄耋老人,但时光的尘土却掩埋不住历史的真实,因为至今在一些住户家里,产于缸窑岭的大缸并不难寻,它们以静态方式保留着那段辛酸的民生印迹。
同兴窑
生于1930年的卢长青已经86岁,看上去依然健康,话题就从他家院里两口大缸开始。
“是早年咱们缸窑岭产的吗?”
“一口是,一口不是,那口大的是,有七八十年了。”
他语速平缓,思维清晰,但对于父辈到这里开窑的具体时间已经“说不清了”,他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粗略推算一下,祖辈来时大致是在清朝光绪年间。最先到来的是他大伯,那时他父亲还在老家开糖坊(做糖果生意),后来听说大伯在东北开缸窑混得不错,就关了糖坊,投奔大伯来了。
他记事的时候,这个窑就已经有三五十年。父亲弟兄三个,老大卢忠华,老二卢忠才(卢长青父亲),老三卢忠齐。在老家山东临沂时弟兄们就有造缸的手艺,随祖辈闯关东来到辉南县缸窑岭(那时此地无名),看到当地百姓腌菜、做酱都要用到大缸,便同他大伯一道开起了缸窑。
但老三卢忠齐对开缸窑不感兴趣,他只想好好种地,因为这里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可以耕种,不像在老家,土地都集中在少数富户手里,他认为只要有地种就不会挨饿。
如此,开窑的事主要由老大和老二张罗。窑址最早选在镇子东面的小水库附近,但不久因为得罪了一帮“胡子”,窑房被他们一把火给烧了。没办法,只好另选地方,两兄弟四处查看,最终选定现在的缸窑岭(当年叫“西大院”)。那时候这一带人口不集中,散散落落,东一家西一家。他们给缸窑起了名字叫“同兴窑”,因为东面有座山,人们就管此地叫缸窑岭。
开了多年缸窑之后,四十多岁的卢长青父亲才娶上媳妇。母亲比父亲小24岁,是父亲花30块大洋从老家买来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那个年代允许买卖婚姻。”卢长青说。遗憾的是,父亲因操劳过度,成家没几年就病故了。“父亲走那年才49岁,我刚好5岁。完全不记得父亲长什么样,只影影乎乎记得大伯是个长脸,个子挺高。”
卢长青听母亲说,小鬼子来的时候抓官差,要父亲出车给他们干活,父亲说没有。骑高头大马的小鬼子拿过一根大棒就给父亲一顿毒打,当时腿都打断了,附近也没有医院,就在家里硬挺着。他大伯一股火上来也病倒了,家里突遭变故,缸窑只好停了。
父亲死后,母亲带着卢长青和两岁的妹妹艰难度日。妹妹16岁那年得骨结核没地方医治,眼瞅着腿一点点烂掉,不久也死了,就剩孤儿寡母。每次他惹母亲生气,母亲就委屈地哭着数落他,说自己25岁守寡,拉扯他如何如何不容易,他也会跟着哭。
那时候的风俗,死了丈夫的女人可以“招夫养子”,但孩子要改随继父姓,卢长青母亲刚烈,虽然改嫁给一个鲁姓的“碗匠”,但一直没让孩子改姓。历经磨难的母亲把卢长青养到18岁,母亲38岁因病离世。
大伯去世不久,有个叫王家坤的人在当地有些势力,花很少的钱就把缸窑买去了,但也只经营三五年,后来又卖给了在伪满洲国当差的蔡村长。卢长青还有印象,蔡村长身边都有警卫,他进出缸窑时带着警卫的模样相当威风,说起话来趾高气扬,“因为背后有小日本给他撑腰。”
他说,后来缸窑又到了刘明轩手里,再后来又换成了翟凤义,不知倒了多少人的手,到翟凤义手里的时候已经是1945年。翟家哥四个,三个哥哥都在“满洲国”当警察,最小的翟凤义在家经管缸窑。那年正赶上日本人倒台,附近的小鬼子都跑了,他三个哥哥也跑到朝阳镇投奔了国民党。翟凤义60多岁的老父亲惦记三个儿子,担心他们遇到不测,就跑到朝阳镇去找他们。顺着样子哨一直往前走,快天黑的时候才走到楼街。这时前面传来密集的枪炮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在那里交上了火,这老头慌慌张张也没处躲,突然,不知哪伙的炮弹飞过来,一下子给打中了,当场丧命。
卢长青早年有个邻居是日本人,名叫“片山郎”,当地百姓都叫他“大片山”,卢家房子的地皮一半是村民老王家的,另一半就是“大片山”让给他的。片山郎表面上是个商人,卢长青看不出他的真正身份,日本没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做买卖。
“看样子在日本也算有点身份地位,说不清楚。他讲中国话,和邻居相处得都很好。不像后来到中国那些日本人,不是东西,专门欺负中国人。片山郎也开了一个缸窑,在离这儿不远的东边,他还养蜂、养鸡,开诊所,好像什么都会。夏天割了蜂蜜也给邻居们送,平时谁家有事也来帮忙,像个过日子的人。但也有一点不好,你要是砍了他家林子里的小树,跟他关系再好,他也会翻脸不认人,直接上来揍你。他说的也有道理,现在你砍了它,再过二十年不就成材了吗。他没有老婆,三个侄子跟他一起生活,年龄跟我仿佛,活着的话也有八九十岁。日本人倒台那年,他们都走了。”
1947年共产党颁布《土地法大纲》,土改运动开始。几经转手的卢家缸窑也遭废弃,窑上的砖被附近百姓扒回了家,窑房也散了架,只留下“缸窑岭”这个虚名一直沿用下来。
一晃就是几十年,他说细想想也没啥意思,72岁那年他不慎摔倒小腿骨折,还不服劲,接上没几个月照样又去地里干活,这两年就不行了。说到这里,迷惘的眼里现出对生命的悲观。
缸匠
以前造缸不像现在这样采用机械化,几乎全凭手工。做缸、做盆、做碗所用的黏土要靠牲口压实,压土的滚子比辗子还大,一匹马都拉不动。缸土先上辗子上压,压细了再用筛子筛,要像面粉那么细才行。和好的泥橛子一块一块堆在地上,做缸时随时取用。
“拉坯的轮子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样,就像老百姓家那个石磨,中间凿上眼,两边有两个爪,下面套上一个带轮的铁圈,再在地上挖出一两米深的坑,把轮子坐在里面,上面装上泥料。三间房的地方能安两个轮子,把头的地方有个‘摇轮子’,上面一根杆子,下面装一根像扎枪头样的东西,一头连接磨上的眼,另一头连接棚杆,一人摇杆,另两个缸匠在轮子上拉坯。”卢长青的描述非常详细。
做缸没有模子,全凭手上寸头和眼力。一口缸光拉坯就需要三节工序,第一节是底部,抠出泥窝,拉出三分之一时要停下来,抬到外面晾晒,等硬实了再接第二节,接到三分之二时还要抬出去晒,如此再接第三节,才算完成缸坯。
这是缸匠的活,到此就算完事,剩下的活要交给“正外”,他负责对缸进行塑形。显然这是一项关键性的体力活,技术要求高。用带把的泥饼子(又称“正子”)在里面顶住,外面拿板子(又称“拍子”)啪啪地打,想要什么形就能打出什么形,有的还要拍出柳条印来。
以前开窑同样实行股份制。如果装一个窑是20个股份,东家占一半(10个),“正外”能占一个股份,“帮外”(协助正外打头一遍)只占半个股份,其他伙计也都有股份,只是占有很少的比例,几个人才能分到一股。
烧一窑有四五百套缸,大缸套着二缸、三缸,里面还有油坛,或者花盆、夜壶之类,光木头柈子就要烧掉几十丈。他记得父亲烧缸的窑就有他现在的院子那么大(六七百平),加上其他作坊,有二三亩地,就在他家仓房后面,如今早已平为耕地,只剩一圈地基醒目地卧在中心位置。
他还能想起窑的形状,整体像个大馒头,直径大概有20米左右。
缸窑岭上好的土就在卢长青家西面的山梁上,他管这种土叫“爱火土”,现在已经被一家养鸡场建了两个大储粮仓占用。缸土用滚子压细筛过就能用,但做碗要用更细的土。早年伐高粱米用的碾子,将底下的辗盘立起来,中间凿眼,穿一根粗木杠,由两头壮牛拉着来回在窑泥上轧,窑泥里注上水,轧好的窑泥去水沉淀,像做粉子(土豆淀粉)一样,不允许有一点泥沙,这道工序非常耗力。
“青黏干”是做缸的好料,他形容就像人被打瘀血的皮肤颜色,发青发紫。还有“黄黏干”,色如土黄,黏腻润滑,这两种料属同一种土质,因无沙成为做缸的常用料。
有的缸外面需要挂釉子,与民主村的泥缸不同,缸窑岭“同兴窑”产的缸主要是瓷缸,做好的缸外面再挂一层油光锃亮的釉子。做釉子用的土也在他家西面的山上,黑土之下,黄土之上,仅一尺多厚的灰白色土层。取出后放进大缸里沤泡,再添加一定比例的烧柴燃尽的“硝灰”,混合成一种糊状物,用刷子涂在做好的大缸表层,晒干后进窑烧制,出窑的缸分别呈红、青、黑三种颜色。
最好是红色的釉。他说,1945年光复的时候还烧呢,他去看过,烧大火的时候进火的那个门就用砖封上了,只在边上留一个小口往里续柈子,烧得最好的就是窑中间那些,能烧出红色,边上那些火头差点的都是黑色或青色,感觉没烧熟似的,有的还有“缸刺”,不太光溜。缸的等级就是依据颜色划分的,依次分成一、二、三、四、五等,卖的时候,同样大的缸价钱会差不少,有的小缸却比大缸还贵。
收藏缸窑
卢长青有6个儿女,他跟小儿子一家住在缸窑岭,儿子靠种地为生。那片已经变成庄稼地的窑址就在他小儿子家的后院,里面还有许多老缸碴,大的都拣出来堆到了地头,小块的就翻到土里作了肥料。卢长青指了指西侧一道栅栏附近,说那里还有不少,可以过去看看。跨过那些苗不盈尺的玉米垅,来到栅栏跟前,形形色色的泥缸碎片与石块树枝混在一起,有的釉光灼灼,有的暗然沉灰。它们破碎的原因不得而知,你可以将它们想象成当年那些缸窑里的伙计,恋恋不舍地守着他们的老东家,诉说当年的苦难。
拾起一小块带棱的缸碴,斑驳的釉质尚可映出太阳的碎光,麟丝闪烁,金色斑斓。从颜色、质地、形态上,可以看出这些窑片种类丰富,款式多样。卢长青说都是他们家做的,最晚也是伪满时候出的窑。
据《辉南县志》记载:“‘中华民国’三月,选送金、铁、砟、磁器等样品参加巴拿马赛会。”若论当地磁器,那时候也只有同兴窑一家,依此可以推断当时的制瓷技术已经具备相当水平。
在辉发城镇周成那间小型陶瓷博物馆里,来自杉松岗缸窑岭“同兴窑”的展品非常丰富。他拿起一只酒瓮,指着瓮底的五个支钉说:“许多瓷器年头久了支钉先没了,看,这些东西的支钉还在,缸底还有窑名——同兴窑。为什么窑名能保留下来,就因为缸底有个坐盘。”
还有一件叫“范”的器物,就是通常说的“模子”,上面刻有鱼纹和人物,可将泥料灌在里面,压实,待泥料被淘范汲干水分,上面的花纹就显现出来,再入窑烧制,多用于花瓶、冥器之类。
甑(zèng)为古代的蒸食用具,为甗(音“演”音)的上半部分,通过镂空的箅与鬲相连,里面放置食物,利用鬲中的蒸汽将甑中的食物煮熟。单独的甑很少见,多为圆形,有耳或无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黄帝始作甑、釜。北人用瓦甑,南人用木甑。” 《茶经》中也有记载,谓甑为一种茶具,“或木或瓦,匪腰而泥。”周成收藏的这件“甑”年代久远,满语称“饭氏黑”,同样产自缸窑岭。
从清朝光绪三十七年(1912年)到1945年的“八一五”,同兴窑的窑名只存在短短三十多年。除了缸、盆、碗、罐等民用盛器,还有用于电线绝缘的电磁瓶、仿锡壶、仿紫砂器、象棋等,可谓琳琅满目。窑匠也很精明,他们有的模仿书画家把自己的名号或商号刻在窑器的下方,类似落款,或为刻印,或为墨书,形态各异。在一块泥缸残片上,就留有“星记”字样,它们有意无意地随着窑器流传下来。
(于建青 作者单位:吉林日报社)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